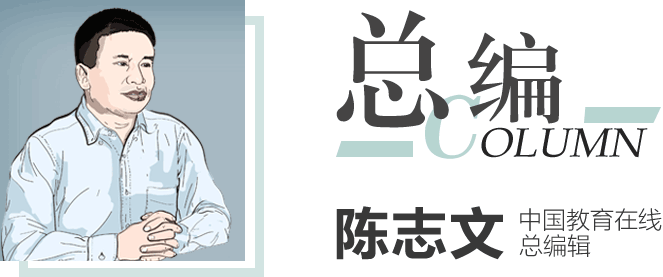最近,四川成都,迎来多所“小初高”十二年贯通式学校和“初高”六年贯通式学校。当地教育局官网相关政策解读显示,贯通式培养是有序推进中考改革的尝试。成都市自2025年起,探索开展相关贯通式培养改革试点。上海市教委于10月20日发布《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将建设一批高质量完全中学和含高中阶段的一贯制学校。显然,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局部创新,而是在国家“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强普通高中建设的政策导向下,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的系统性改革实验之一。
当前,不少专家呼吁将义务教育向高中阶段延伸。事实上,我国多数地区已基本具备普及高中教育的条件,特别是在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国家层面也明确提出将向“两头延伸免费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表述是“免费教育”而非“义务教育”,因为后者具有强制性。目前,向下延伸至幼儿园的免费教育已启动具体补贴措施;而向上延伸至高中,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两个核心问题:中考以及普职分流。
2024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92.8%,从数据上看高中教育已近普及,但问题在于:许多民众并不将职业高中视为真正的高中。针对普职分流的争议,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设“综合高中”,即推迟分流节点,让学生在高一保留普通高中学籍,至高二年级再根据个人选择分流至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路径。
然而,这仍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即中考背后的高中择校问题。谁进入由职高转型的综合高中?谁又能进入上海中学、学军中学之类的名校?录取依据是什么?部分专家,尤其是非教育领域专家在呼吁“取消中考”,但现实操作难题如何破解?难道要靠抽签决定?
在此背景下,包括完中建设在内,一贯制学校被视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实验价值确实多元:它有利于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特别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连续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规避中考带来的应试教育干扰。同时,它在理论上也能绕开或部分绕开中考这一环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和学生的焦虑与负担——这恐怕也是其受到许多家长欢迎的重要原因。但是,上海、成都当地教育部门都急忙澄清此举并非取消中考。事实上,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是一个小众试验。
关键在于:取消中考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与负担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至少不宜过度乐观。以中高考为代表的教育焦虑及相应负担,本质上是社会竞争在教育阶段的前置投射,其根源不在教育本身。且不论一些好的用人单位招聘时对毕业院校的严格设限,各地组织部门选拔选调生时,同样明确限定毕业院校范围。这种“出身标定”本质上是以教育评价替代人才评价,以分数门槛简化能力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学生不得不在教育通道中提前展开激烈竞争,只为获得最基本的入场券,尤其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性思维,不能仅表面化地看待教育焦虑。即使取消中高考,我们也无法取消社会竞争,自然也无法消除竞争带来的焦虑与压力,无非是其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已。如今“国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正是这种焦虑转移的明证。
更复杂的是,这种焦虑是一个系统性难题,不会因某个环节的取消而消失。取消中考,或许能缓解中考直接带来的压力,但后续还有高考这一关。难道我们也要取消高考?历史经验表明,当年取消小升初考试后,小学生的升学压力并未真正减轻,反而转化为更疯狂的校外培训热潮。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前,教培机构的核心客户群正是小学高年级学生,而非中学生。这恰恰说明:竞争只会转移,不会消失。
此外,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本身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入学资格如何确定?抽签还是划片?中间转段机制以及如何保障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我们固然应当鼓励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探索与实践,但切忌过度理想化,为其赋予它无法承载的改革目标。更不能因理想化期待而扭曲实验本身的方向。教育改革需要实事求是,在缓解当前焦虑的同时,更要直面其背后的深层矛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渐进改善中寻找真正的出路。
本文首发于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