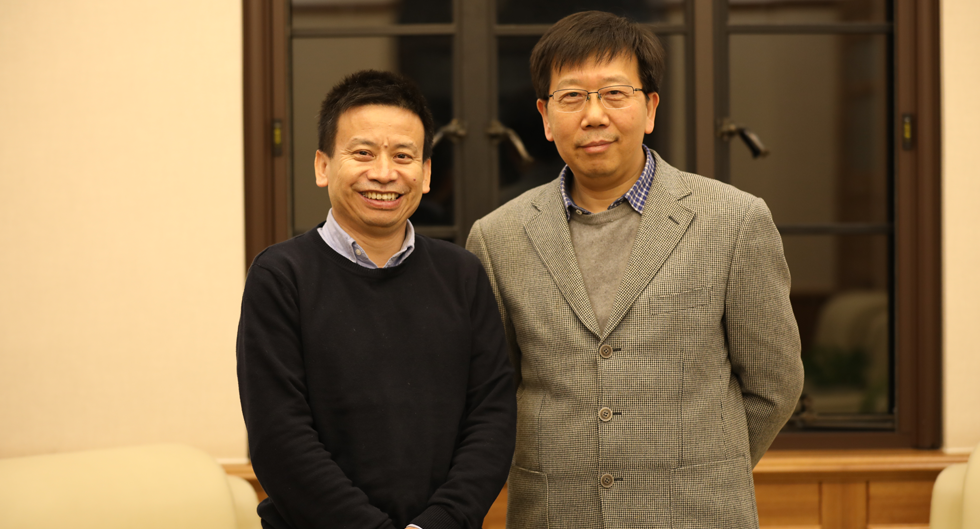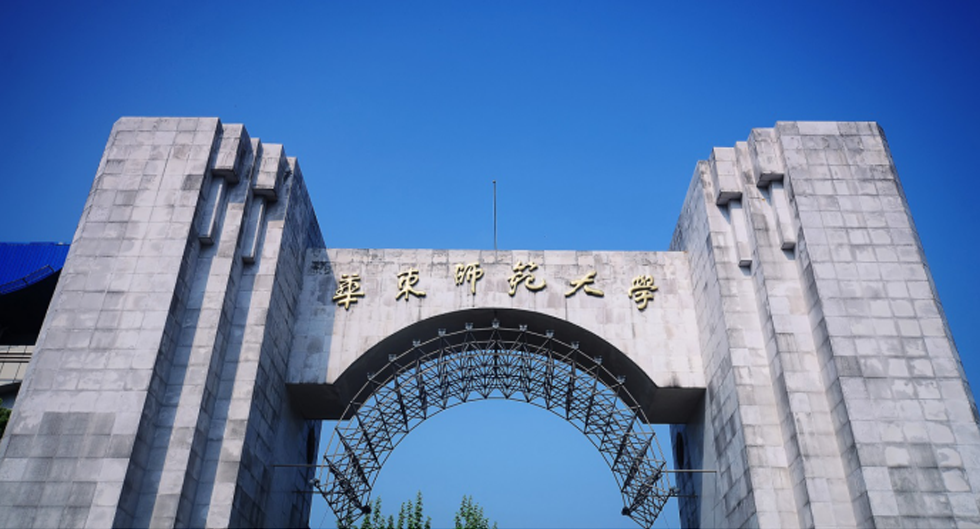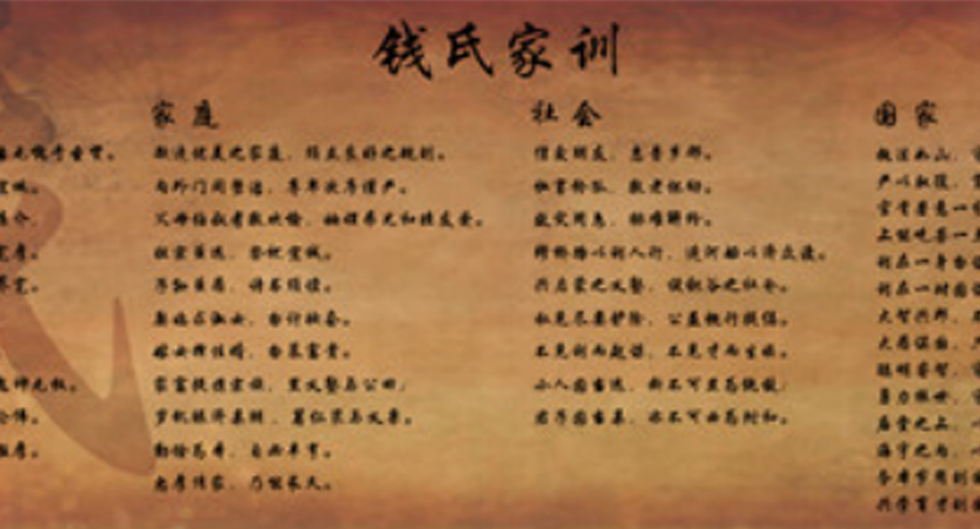钱旭红:
对我来讲没有特别大的冲击。虽然两所学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对两所学校环境的转换,我接受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
华东理工大学是一所非常强调执行力的高校。,我担任校长期间,曾强烈大力推动华东理工大学参与国际认证,并成为了国内第一所通过国际工程教育认证(ABET)的大学。该校也是我的母校,除了在国外和在大连理工大学的岁月,我在该校断断续续度过了33年。该校化工类专业培养出的学生大多心细胆大、敢冒风险、敢于承担,且具有很强的团队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的特点是多学科,是一所包含艺术和体育的真正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更是一所教育领先的大学。相对来讲,人文社科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强项,当然理工也不弱。所以,比起华东理工大学,更强调价值、理念和人文关怀。
其实,每一位学生在读大学期间都会打上本专业、本学科的烙印,并且会改变他或她的性格。一所大学不会只有一种性格。当一所大学里有多种性格存在时,就证明这所大学是健康的。如果一所大学只有一种性格,那就麻烦了。
说到挑战,大家一般会认为,工科大学的校长对人文社科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当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呢?但其实,我对人文社科是很尊敬的,这几年我写的文章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我高中阶段对文科感兴趣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写东西时文字很朴实、没有浮华的词藻,但是会更注重独特的思想、清晰的主线、精确的表达、严密的逻辑。
钱旭红:
一所大学必须要有愿景和使命。华东师大的愿景,就是分三步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校领导集体的支持下,我推动了学校理念更新,确立和明晰华东师大肩负的三大使命,即育人使命、文明使命、发展使命。
第一是育人使命。华东师大是一所独特的学校,以教育为特色。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老百姓仍然对教育有很多抱怨,党和国家仍然对教育还很失望,即便那时华东师大所有的指标都在全国遥遥领先、名列国际前列,也不能算是成功。因为,华东师大、北师大这样的大学,肩负着改变教育的责任,肩负着育人使命。
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现在的育人模式,培养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要站在党和国家的站位上,用专业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解决千家万户的烦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范类院校的失败。因此,这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要做的第一方面的事情。
第二是文明使命。关于文明,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狂妄自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文明在近代曾面临逐步衰败、,乃至可能消亡的危险。几千年前,西方文明从东方文明中吸取了养料,才蓬勃发展了起来。但到了近现代,我们是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比如,现代大学的学院分布、知识体系,就是源自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形成于三百年前的欧洲,之后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
接下来,我们如何才能对世界文明作出较大贡献?在我看来,只有建立能够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体系,才能使我们赢得真正的自信,也才真正能为世界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世界文明作出较大贡献的文明使命。
第三是发展使命。我们需要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发现新的工具和力量源泉。到目前为止,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重要工具和动能都不是源自中国,比如发动机、蒸汽机、化石能源、核能等。今后,我们要创造能够推进社会发展的新工具、新源泉。
比如生态,如果人类社会能够很好地与生态相融相处,形成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就能够既实现工业目标,又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比如人工智能,智慧是人类社会的最大资源,中华民族是具有人类最高智商的群体之一,人工智能可以进一步跨越人口红利,解放人类的智力资源,这也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再比如大数据,我国人口众多,产生了的数据海量并多样的数据,这就为我们开发用于发展的“数据能”(即大数据资源,犹如矿山资源,将成为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可能。综上所述,寻找新的发展工具和发展能量来源,就是我理解的发展使命。
钱旭红:
我希望用三年的时间建立起雏形,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还有两年。其实,这三大使命最后凝聚成一句话,就是我在华东师大提出的“幸福之花”的概念。“幸福之花”更多的是指对社会的关爱,是要为校园、为全社会提供幸福的解决方案,也是“爱在华东师大”的真正的诠释。
就“幸福之花”的落地方面,我们目前主要聚焦五个领域,也可以说是华东师大“幸福之花”的五个“花瓣”。首先是“教育+”(Education Plus),即所有学科都要支撑教育,教育要辐射多个学科。这一方面涉及到学科之间的融合。比如,要思考如何把教育模式和脑科学相结合,如何把闲置的智力资源激活。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实践教育,包括双创。没有实践,人是无法立起来的,教师要教给学生实践技能。
另外四个领域是“生态+”,“智能+”,“国际+”,“健康+”。我们不求在所有领域都能完美,但要在这五大领域取得突破、取得明显进展。
钱旭红:
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上海洋山深水港自动化码头,被称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无人码头。华东师大在该项目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该码头负责决策的管理操作系统中,一些重要和关键性的算法和程序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完成的。
第二个是浦东机场。当时浦东机场在选址时,华东师大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出利用滩涂资源,在潮滩上建设机场,大面积节省了耕地,另一方面另外也提出了九段沙种青引鸟的生态工程,很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